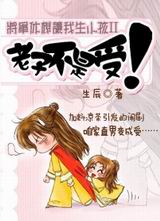我生有涯愿无尽-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福。我忙指给身边的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的,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1月12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的。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26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八、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的。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28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4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悉的。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缘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的感想。一中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的。)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1928年)7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1926年)6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知)、徐先生(铭鸿)主持。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班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我叹息,尽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9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4)
九、处险境中我的心理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亦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忧急恐慌的,其幸福又有几何呢?
二十八年(1939年)我去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
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任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么》(最近在香港发表)三书出版,已见大意,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实现。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一班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它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么,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
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我处险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长进,再去理会。
后记
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指《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0节 回忆调查李闻案
1946年初与民主同盟部分同志合影。前排自右至左依次为:史良、张澜、沈钧儒与作者。
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接连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一、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张的时候。
李公朴被杀害的消息于12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像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