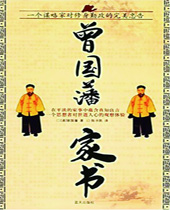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 “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地方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在还没有实力与太平军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曾剃头”的由来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
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咸丰帝又下旨,说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认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把恶心铲除,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从而让地方得以安宁。浏阳、攸县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抚认真查办,并与在籍侍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所有这些都说明咸丰帝为剿匪一事忧虑万分。
因此,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在这篇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由于在奏折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匪徒几近残忍的话语,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所以咸丰帝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来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湖南匪徒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