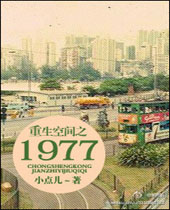5898-妖娆罪 :滇西驿妓的红尘往事-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遥远的境界。我此刻期待一种现实: 我希望站在身边的斑鸠和鸽子,她们中的一个人能够用身体的力量把白爷带到卧房中去。
如果那样的话,面前呈现出来的看不清楚的一场骚乱就会结束,它渗透不到未来,尽管未来对我是缥缈的,然而,如果没有白爷的降临,也许我的未来会变得单纯一些。我试图为自己创造这种潜意识中的单纯,如果吴爷照此这样控制住那个像火焰一样流窜的阴谋。我既然有权力产生那个阴谋,我当然也会理性地减弱那个阴谋的存在。这取决于我在驿馆的现实,眼下,吴爷是我惟一的男人,他的银票已经决定了我身心的某种自由,所以,我曾希望在吴爷从马背上归来时,我是他的肉欲之乡,而当吴爷离开时,我又是驿馆中生活得最任性的女人,每天黄昏我用不着站在门口迎客。
我只为吴爷献媚。而此刻,局势变幻: 在姚妈的力量操纵下,我又要变成献媚者,这个局势使我的抵抗力不从心。即使是斑鸠和鸽子的献媚,倾尽力量的献媚术,对白爷来说也显得徒劳。白爷伸出手来,他可以左右自己的选择,我注意到了男人们的一种姿态,当男人站在驿馆门口伸出手来开始搂紧一个女人时,这个男人已经为他的夜晚选择好了纵欲的伙伴。
白爷伸出来的手惟愿随着缕缕的黄昏而去,我早就已经感觉到深秋过去了,它是随同吴爷的影子过去的,当白马纵身跃出驿馆时,我感觉到深秋越过了我的窗棂。而此刻,我希望白爷的那只手,一个男人坚定的手拥有它的选择,而斑鸠和鸽子可以任凭他去选择。
《妖娆罪》第一部分诱骗记(5)
当白爷的手——那只坚定的手臂从深秋的坠落之声越过模糊到达我的腰肢时,我知道,我的本能又一次开始了抗拒。白爷搂紧我的腰肢时,我的眼前一阵晕眩,我提炼不了一种素质: 在这个黄昏,附属于另一个男人,成为这个男人的玩偶,也许这一切都因为吴爷的存在,以及他对我始终如一的占有,使我已经失去了一个驿妓特有的职业素质。
姚妈消失了几秒钟以后,亲自捧着一碗蜜糖水来到了我身边,她示意白爷先松开手,然后一定要看着我亲自把那碗蜜糖水喝下去,姚妈说我的身体看上去有些虚弱,仿佛失去了糖分,女人的身体是靠大量的像蜜糖一样的东西在支撑着,缺少了蜜糖,身子骨就支撑不了时世和命运的变幻。
当我用舌尖品尝着那些蜜糖时,我并不知道姚妈的另外一种魔幻已经在我的身体中产生了魔力: 驱使一个束手就缚的拘谨的女人,在一刹那间燃烧起来情欲。这就是那碗蜜糖水产生的功能,它成就了姚妈的诡计,实现了姚妈配方中的催情术。
蜜糖尽快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中,我渐渐地失去了力量,突然,当白爷再一次搂紧我的腰肢时,我仿佛看到了吴爷,我有权利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吴爷,久而久之,吴爷已经成为了我的男人,就在我们回到卧房时,我的身体触到了白爷身体上的一种坚硬的东西,白爷看见我不舒服便解下那东西。我的恍惚,我的被蜜糖水似的东西所溶尽的血液都上升为一种情欲。就这样,姚妈凭着一碗蜜糖水就已经改变了我的目标,让我和白爷度过了完整的一个夜晚。
拂晓临近,蜜糖水的功效已经在我体内慢慢地失去了魔力,我渐渐地睁开双眼,发现一个男人躺在我床上,我惊恐地爬起来,想辨认这个男人是不是吴爷,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意念和幻景之中,我始终是在跟吴爷过夜。
我没有看到吴爷身上的那道伤疤,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看到的就是一团模糊和陌生的肉体,我还看到了那坚硬的东西,当我刚伸出手想去触摸那件东西时,白爷翻过身来再次搂紧了我,他的气息裹挟着一种烟叶味儿,他体贴温存地对我说:“你的手只能触摸我,你是女人,女人是不能玩枪的,你果然像姚妈所描述的那样很狂野,像只狐狸,我遇到过很多女人,但都没有你这般的狂野,刚刚逝去的一夜,你在床上是够狂野的啊,你有可能会让我忘记别的女人……”
我后来才知道那蜜糖水不仅仅激起了我的情欲,也同样激起了我的狂野。就这样,在吴爷离开的日子里,白爷趁机占有了我的身体——这使我的好友斑鸠和鸽子失去了一个时机,她们在私下扬言道,如果没有我在场,白爷就会钻进她们的卧房中。她们私下诋毁我,说我是驿馆最自私的女人,总是想占有最有权威的男人。而我却在私下产生了一种念头,如果斑鸠和鸽子能够占领白爷的身体——那么我就获得了自由。
我的自由是吴爷给予的,他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个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男人,当翡翠手镯在我纤细的手腕上滑动时,我总是想着吴爷,我甚至会眷恋他身体上的那道伤疤。我想,别的男人无法与吴爷相比较,因为吴爷跟别的男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已经占领了我的身体。
白爷与我度过了三个夜晚,决定带我出驿馆到外面透透气。他感慨道:“驿馆虽然很快活,却始终是一个女人的世界,我想让你看一看男人的世界,看一看我白爷的世界。不管这两个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今天都想把你带出门,你愿意吗?”我不假思索地说道:“我想,我愿意。”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再次有机会出驿馆,这个死灰复燃似的愿望此刻使我的灵魂浮出了胭脂和舞动的香帕之上: 它已经从姚妈的重重诡计中再次冒出来。我的那个阴谋,仿佛就是从我身体中再次长出来的幼芽。淡绿色或鹅黄色的胚芽是我灵魂中的再生之地。一旦白爷带我出驿馆,这个胚芽将越过沉重的尘埃,我相信它一定会自由地生长。当我被白爷抱在马背上时,那匹黑马在那个早晨成为了驿馆中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我看到姚妈站在驿馆的中央,她的翠绿色的丝绸长裙并没有随风舞动,因为在那个早晨没有一丝风儿,所以,我能够感觉到翠绿色丝绸仿佛一种死寂生硬地贴在姚妈成熟的肉体上,使她在那个早晨显示出一种我从未看见过的欲望。姚妈的最大欲望就是竭尽全力地控制好我们肉体的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这个早晨已经绽放出一种旋律,我后来才知道白爷的降临使姚妈不得不屈从于一种东西,因为白爷的身份与降临驿馆的商人不一样,他是拥有一支土匪队伍的白爷,他拥有让姚妈畏惧的武装设备和一支失去了道德规范的队伍。所以,姚妈把我拱手献给白爷。我还看到了斑鸠和鸽子,她们的身体倚依在楼道的木栏之中,她们挥舞着香帕,试图不放弃每一个机会,以此让白爷猛然回头时,看见她们鲜活肉体的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让许多男人心花怒放,当然,也同样可以让白爷心花怒放。除此之外,在这两个女人的目光之中同样充满了嫉妒和失落,她们原以为白爷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的再现。因为,我早已发现一种趋向,进入驿馆的女孩子一旦被姚妈训练以后,她们就认命了这种现实,从而开始垒造自我的另一种价值。也许,在她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女人,我不费工夫就得到了茶叶商人吴爷的宠爱,现在又赢得了白爷的垂青;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男仆们簇拥在门口,目送着白爷。从这种局势上看,白爷是一个重要的人。
一匹如乌云一样黑的马,显得高大强壮,当我的身体落在马背上时,白爷跨上马背搂紧了我,在这种意义上讲,吴爷和白爷具有同样的东西,他们都想带着他们的驿妓走出驿馆。只不过,吴爷让我骑在白马上时,还没有占有过我的身体,我不知道那天黄昏,吴爷是怎样滋生一种随风飘动的情绪,想带我在驿镇遛一圈。很久以后,我回想起这种场景时,依然能感觉到吴爷的那种情绪在我身上飘荡着。白爷却不一样,他跟我度过了三夜才决定带我到驿馆外面去,到他生活的巢穴中看看,以此证明他的身体和价值。
黑马纵身一跃,我的身体就离开了驿馆,如果我阴谋中期待的那种自由就在黑马驰骋朝前时展现,那么,生存下去是多么美妙的图景啊。白爷挥动着缰绳,他跟吴爷不一样,他不愿意环绕着驿镇,他的黑马纵身一跃之中,我们已经过了驿镇的通道。
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我没有嗅到泥土和庄稼弥漫出来的浓郁的气息。在很长时间里,我被迫缩在笼子里,我仿佛已经失去了双翼,我仿佛被折断了幻想的翅膀。而此刻,我放眼眺望着盆地上错落有序的房屋,以及飞翔在天空中的第一批候鸟,惟愿我的肉身落在大地之上,落在敞开的我心爱的滇西北的盆地和丘陵地带,哪怕我是一只受伤的鸟儿,我也可能飞翔起来。
白爷的手时而松弛时而搂紧我的腰肢,我想要从马背上逃逸而去是很难的。我只有等待时机。自从进入驿馆以后,我仿佛是一个经历了迷乱的女人,每时每刻都在与迷乱作斗争。所以,澄明迷乱的最好办法就是逃离驿馆。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再次降临到我身上,所以,我绝不会从马背上纵身出去,因为我知道,白爷那只鹰爪一样的手掌会将我从半空拉回来,我既不会死,也不会生,我绝不要这样的过程。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要付出代价和思虑。此刻,我让白爷搂紧我,随同黑马纵身的节奏把我载向一个纵深的峡谷,这就是白爷的巢穴。当我从马背上落到地上时,我看见峡谷周围站满了持枪的男人们,这就是白爷的土匪巢穴。白爷把我带到一个洞穴深处,眼前升起的幽暗使我感到一阵寒气袭来。
白爷登上玉石雕成的宝座,旁边侍卫递给白爷一根水烟筒,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闲暇时都会眯着双眼吸着水烟筒。我想起了生活在岗寨上的父亲,从我出生时,父亲就一直手握住金黄色的水烟竹筒,有些女人也会仿效男人的烟瘾,他们蹲在一道道阴影中,不断地吸着烟筒上被点燃的黄色的烟叶。
白爷让我坐在他身边,我想趁机到外面走一走,因为我知道滇西的男人们吸着水烟筒的时候,也是他们神经最为松弛的时候,在白爷神经最松弛时逃离而去,倒是一个难得一遇的时机。于是,我沿着大堂的一道窄门移动着脚步,我回过头去,目光与白爷的眼神碰撞在一起。我想,这正是我寻找到的机遇: 白爷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我想,他放松了对我的警惕,他的目光和心态如今正沉溺在滇西特有的烟叶香味之中。
《妖娆罪》第二部分幽魅记(1)
当我的脚步在错落声中踩着腐烂的叶片进入一片林中地带时,我回过头来,我似乎终于摆脱了白爷的岗哨。起初我溜出大堂的窄门时,曾经有几名手扶枪支的岗哨跟踪我,我从怀里掏出一些银两,我没有想到当我小心翼翼地把银两展露在我掌心时,一个又一个的岗哨顿然间目光闪烁。
一种最世俗的简洁交易使岗哨们从我影子后面撤退。我回过头去,似乎离岗哨们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有些慌乱,似乎往日虚幻的一刻被我扭转了,从我身边延续出去的路过于明媚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心中暗想: 人都有疏忽的时候,白爷此刻正手捧着烟筒,那种迷幻的烟叶自然会麻痹白爷的神经。
正当我积蓄起我的力量朝着一片林中空地奔跑起来时,我发现了一只逃窜的狐狸,我在岗寨的山冈上远远地见过这种狐狸。那时候,我只有六岁,寨子里的人们互相传播着狐狸进寨子了,让大家手持棍棒把狐狸赶出寨子去。于是我们就跟在大人们的身后,也就是跟在那些舞动不休的棍棒之后,去观看这场驱逐。当我们远远地眺望到那只狐狸时,那只褐色皮毛的狐狸站在一座石岗上,注视着我们,突然,它的身体朝石岗猛然跃起,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只狐狸。
眼前的狐狸似乎也在逃窜,它焦躁不安的目光离我们很近。就在我虚妄的愿望在一只林中狐狸身上得到再现时,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那只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林中狐狸在枪声中倒在了那片金黄色的腐叶上。
白爷拎起那只狐狸,走上前来对我说:“如果这只林中狐狸没有与我相遇,也许它还能拥有另一种命运……这就是命运。就像我现在面对你一样,我知道,你想跑,然而,乌珍,我告诉你,在我眼下,你是无法逃出去的……”
1929年的冬天是我生命中最为寒冷的时光。每天我和驿馆的女人们一大早忙着生一只火炉。在那些黑乎乎的柴炭运往驿馆的杂院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