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销售量。而1999年的销售报告一出炉,甚至让日本新闻媒体玩起了文字游戏:日产(Nissan)从第“二”(ni)掉到了第“三”(san),日本第二大车厂的地位拱手让给了本田汽车。而日产在日本各个工厂的产能也降到只剩下原先的五成。在过去八年的会计年度报告中,有七年呈现赤字。总结果如下:总营运债务(不包括给予客户的延长贷款)达到二十一兆日元,约二百亿欧元。日产保有其一贯严谨的工程部门所获得的优良名声,但是其产品设计之平庸却完全不受买家的青睐,所有车型中只有一款登上日本十大畅销车款。
为了了解日产究竟为何沦落至此,戈恩花了几乎整个1999年的春季仔细检查日产在海内外每一座办公室、工厂、技术中心、经销商、供货商及消费者等各环节的状况。这前几个月的工作又让这位尚未成为总裁的老外得到一个新外号:7-11。和这家遍及日本各地的连锁超市一样,他每天清晨即开始工作,等他下班时太阳早已经下山很久了。
7-11式的日子是从1999年4月开始。在那一段期间内,我密集性地工作,做了一堆分析及摘要的工作,以便整理出振兴日产汽车计划的大方针。我花了许多时间会见许多人,走访各座工厂,拜会各家供货商。不仅在日本国内拜会,还到美国、欧洲、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去。其实我一直在四处考察,并多次返回雷诺作短暂停留。也可以把这段时间视为暖身期。考察行程安排得很好,让我得以与各不同层级的人事负责人会面。他们为我说明了公司的情况:哪些进行得顺利,哪一些不顺利,然后询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试着分析一项并非恒常的状况,但是该状况却能鉴别出,什么是有效改善公司营运成果的要件。这段期间我也听了很多,但不是被动地听,而是主动去倾听;也做了许多笔记,带回很多数据,里头有很多我们碰到不同状况时得到的详细数据,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做整理。那三个月里,我所见过的人真是数不清。我记得很清楚,藉由这成千上百的会面与谈话,自己一步步地建立起对公司的完整印象。即便我一直在修正这个印象,但其实最初的印象已经和日产汽车的实际状况相去不远;中长期的表现逐渐地印证了此一印象,而我自己也发觉这个基本印象并未偏离公司的实际状况。
先前也曾是车厂供货商的戈恩相信,从长期合作伙伴那里得知对于顾客的看法,往往最是一针见血:供货商和车厂的关系近得足以看清实情,而同时距离又远得让他们能毫无顾忌地说实话。
我拜访的每一位供货商都非常坦率,让我十分惊讶。他们一直都想找人谈谈,谈他们和日产的关系,因为日产的状况实在让人忧心不已,而他们也衷心期盼能见到日产重新振作起来。日产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是无庸置疑的,这些人——从高层主管到基层员工,每个人都对日产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日产墨西哥厂的周遭有一些天线供货商,我和他们一起举行会谈,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最客观且贴近事实的现况,也让我注意到日产在采购及库存方面的凌乱与离谱的状况:一座年产量达二十万辆汽车的工厂,竟有六家不同的轮胎供货商!供货商们抱怨日产常在定出目标之后,又在三个月之后修改了该目标。还毫不避讳地照实告诉我日产汽车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他们话中的意思是:“是你们自己把日产搞成这样缺乏竞争力的。你们下的订单总是非常零散,也从不听我们的建议,即便是品质缺乏保障,也总想自创规格却不采用标准规格。日本厂有日本厂的供货商,美国厂和欧洲厂又各自有自己的供货商。是你们自己建立了这一套完全没有效率的体制。很自然地,你们也就只能找到和你们习气相近的供货商。”而这些供货商大部分是日本厂商,其中又多是日产的子公司。一旦抛开客套话,他们失望的程度便完全揭露在与我之间毫无障碍的坦率对话中。
第一部分:迈向亚洲企业体检与诊断(2)
在日本,接待访客往往有一套规矩。总是有一间会客室,在工厂里也不例外。室内的摆设装潢总是千篇一律,日本各地全是一个模样:铺着缀有花边的垫子的大张沙发、低矮的茶几,身着制服的女职员端进一杯绿茶,再静悄悄退出会客室。
他们把我当成总裁一样接待我,一面奉茶一面跟我谈论天气。是我主动打破僵局,跟他们说:“您太见外了,跟我说实话吧!您觉得这家公司的问题出在哪里?”当他们明白我确实很坦率,想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时,便开始毫不保留地说出来。数个钟头的讨论内容真是非常令人兴趣盎然。我认为能和他们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话,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忧心日产的状况。不用说,他们对于计划成效多少抱持一点保留态度,但是仍然配合日产的计划。
在这段考察期间令他深刻印象的若干次会谈中,有一次是拜访日产的工会组织。和其他的日本大企业一样,日产汽车也设有工会,由同业行会所扶持,所有专职正式员工都必须加入该组织。日产内部的气氛并非一直都是那么令人放心。在1953年时,日本才刚刚脱离被视为是压制工会组织与极端反共势力的美军托管期,日产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罢工抗争;罢工持续了五个月,惊动日本各大企业老板,并使他们全力在幕后支持日产的董事会。该次罢工最后因为其中有人向极左派示好而终告失败,但是新的工会组织则崛起掌握罢工的权力。
7月时,工会要求与我见面。那时我才刚刚被任命为营运长及日产理监事会的成员。整个日产工会的干部都来见我,我们相谈甚欢。先前人家将日产的工会描述得太让人忧心了。那次的谈话让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彼此毫无保留。他们当中有一名代表在会谈接近尾声时对我说:“我们受够了这堆计划,尤其是那些计划完全行不通;目前为止的所有计划,没有一项是可行的。这家公司在不断失血,员工们都很担心,得让日产走出泥淖。只要你的出发点具有建设性,并且重视我们的意见及看法,我们绝不会阻挠实行振兴计划。”和工会成员的首次接触让我放心不少。他们只是在扮演工会的角色:也许不是很亲切,但是实际上却很积极正向。我因此而安心不少,精神也为之一振。我早知道一定得获得他们的信任,但也明白他们有妥协的准备。我要面对的人并非是不讲理的人,他们也对日产的状况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所传达的讯息是,只要我是认真想挽救日产,他们绝不会故意从中作梗。这和在其他国家里跟工会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不同,我对此真是大感意外,而我向来是不轻易和工会打交道的。工会的存在,其地位是很重要的:得要倾听他们的诉求,要开诚布公地向工会说明公司所要做的事情。但是相较于别人对我描述的工会状况,这次和工会的会谈,倒像是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心想这群人是可以一起工作的人。
在头几个月里,戈恩大部分的时间待在基层,而不是躲在他那位于银座总部的第十五楼里。尽管情况十万火急,但是公司的行事历并未因此而有所更动,得等到六月底的公司股东大会上,卡洛斯·戈恩、堤耶利·穆隆凯及派屈克·普拉塔才会被任命为新的监事会成员。在此之前,这位未来的营运长一直在灰色地带游走。
我在四月抵达时,日产旧理监事委员会还存在着。我完全没有参与任何一项会议,因为我那时还不具备正式的职衔。我时常和义一保持联系,他跟我说已经答应路易·施维茨,将会改组理事会。还征询我对于理监事会成员有没有什么想法,而我并未就新的理事会组成提出任何一名人选,理由很简单:他们里面,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只是告诉义一,我完全信任他的选择。
而事实上,结盟的第一项后果便是迫使日产汽车必须严格执行理事会瘦身计划。1999年4月28日,日产汽车公布新的领导组织架构,理事会编制将缩减为四分之一,由三十七席减为十席。成员数量庞大的理事会呈现出日式管理的怪象:理事会并无法代表所有股东,只不过是公司高层主管的延伸,只要年资足够,最后就能成为理事。只是一种酬庸,完全不在乎这个人是否有能力为公司作出有贡献的决策。如此庞大的编制,其作用在于屏障总裁的绝对权力及围绕其四周的核心份子。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美式企业管理观念开始被引进日本,并且在诸如索尼(Sony)等先进企业率先被实施,同时还缩减理事会的编制。
有这么多理事,很难让人想像日产的管理是怎么一回事。再加上这中间有一道语言障碍,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说得一口流利英语。我们之间的管理经营观念差异太大了,对西方人而言,这显得非常神秘。但我所秉持的原则在于,面对一家二十多年来在市场占有率不断下滑、累积了大量债务、难以获利的企业时,要先确认这些问题的本质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部分:迈向亚洲企业体检与诊断(3)
卡洛斯·戈恩所坚持改革的是真正经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架构,特别是该会成员必须改组。
为了进行重大调整,我介入若干重要主管的任命案。尤其,我希望有一名负责采购的执行副总裁,而他只要专心这项工作。在仔细研究了每个人的背景资料之后,我坚持要由小枝至(Itaru Koeda)出任此一职务,虽然我个人还不认识他,但从他的背景资料可看出,他是最佳人选。执行委员会也将成为我的班底,但是人员并非由我挑选,是义一选出了所有成员。他很重视我对于如何组织此一委员会的想法,不过我当时完全无法对这些人作出任何评语。最后,我只更动了其中两名成员:九名成员里更动两名,幅度不大,其他成员都是一时之选。
即使整个夏天还必须继续到各处考察,到了1999年6月底,整个企业健诊期基本上算是告一段落。
从这次的巡回考察中,我感觉日产的问题是出于组织零散及讯息混乱上。原本即感觉到公司在讯息传递上很混乱:员工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只好东凑西凑,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缺乏先后次序、也无条理可言;每个单位各自为政,就像一盘散沙,彼此没有一点交集,也毫无默契可言。工程师们对于产品的认识非常深,技术也非常精良,但这样还不够,想更有效率,就得对汽车产业具有洞烛先机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得重新建立起这种能力。哪些事情是必须优先处理的?哪些人负责什么事情?这一切都还非常模糊、抽象。我心想,不是我就是我周遭的人得花时间把这些问题给一一揪出来,以便让每个人都能看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事。
把过脉之后,再来就是要诊断病情。
这么一家以技术能力著称的车厂,过去曾表现其高超的创造力,尤其是在技术及设计方面的能力。这样一家日本企业之星究竟为何落到这般田地?这个问题无法从20世纪80年代呈现泡沫化衰退的日本经济状况中寻得解答,因为丰田以及本田这两家同国籍的车厂都已从该经济危机里全身而退。问题的症结一定是跟日产本身的历史有关,不过雷诺特遣队的工作并不是来这儿进行考古工作的。很显然,不要对一家已经走下坡的企业在管理方面有所期待。
老实说,我在公司里从没遇见有哪一个人能为我把日产的事迹作精辟的分析,没有任何一个点能将公司解释得很明白,没有一个人能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把问题说给我听。这家公司在管理方面就是一团乱,这是排名首位的难题来源,而且只要在一家公司里发现这样问题,马上就可以知道就算这家公司的营账还未到病入膏肓的地步,离这种状况也不远了。
不过,得看清这一点,而且速度要快。路易·施维茨曾说过这句话:“我们很急,因为我们规模小,财力又不十分雄厚。”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家公司衰退到这个地步?哪些是我心中认定的主要因素?首先,日产太过以自我为中心而失去追求利润的方向感。经理人对数字毫无概念,也不清楚营运成果,完全没有明确而量化的目标,他们在卖出车子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赔本或根本没有利润。只有少数人注意到这个核心问题,但他们也只有概略的资料。即使有人谈论到收益,但这也从不是公司所关心的焦点。当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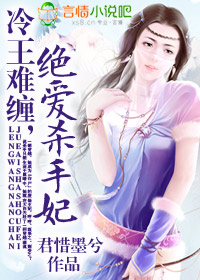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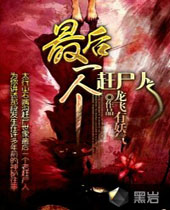
![[快穿]给我一个吻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0/7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