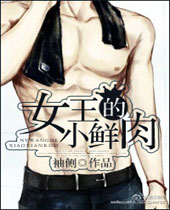紫禁女-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暗中,吴源已经急急地掀开被子,分开我的两腿。这时,我们家的猫忽然在窗前“咪啊呜”地叫了一声。
他忙乱的两手立时停住了,直起腰竖耳静听。
我有些冷,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兴许这个动作唤醒了他,他略加思索,终于心一横,义无返顾地一跃而上。
…………
“你,还好吗?”我嗫嚅着问。
“唔。”他含糊道。
“我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悄声说。
他这才扭过头来,心有不甘地道,“你怎么会有感觉呢?我都没能进入。”
“什么?难道你……”我既惊讶又懵懂。
“不过,也许是我自己……”他说,语气很有些颓然。
我忽然有些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儿,感觉着他身体的那个部位又温热、坚挺起来,我便说:“你要再试试看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还是爬上来。
然而,上上下下许多次,折腾了差不多半夜,他已大汗淋漓,但仍不得要领。他看上去很有些垂头丧气,终于放弃了,翻下身,在我身边心不甘情不愿地休息了一阵。
后来,天快亮了,他忽然央求我:“玉,我能看看那儿吗?”
“干什么?”
“我就想看看嘛。”
“有什么好看的。”我说,很不情愿,但看他很坚持的样子,还是默认了。
我因为害羞,本已闭上眼,忽然感觉到他一阵哆嗦,冰凉的台灯一下子砸在我的大腿上。
“怎么啦?”我睁开眼,欠起身。
“没,没什么。”他支支吾吾地掩饰。翻倒在床上的台灯灯管正好映照着他的脸,看上去一片惨白,目光里更掺合着一种异样的莫名惊诧。
“告诉我,到底怎么啦?”我再问。
“什么?唔,没什么,我想,我是有点累了……”他吞吞吐吐地说,注意到翻倒在床上的台灯,忙拾起来重新置回到床头柜上,然后缓缓地仰面躺下,头枕双手,陷入沉思。
直觉告诉我,确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确实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于是支起胳膊坐直起身。
“……?”我用我的目光向他询问。
“……”他也回望着我,几番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体检吗?”
“体检?什么体检?考大学时做过的。”我说。
“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有没有做过妇科检查。”
“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他又不吱声了。
我们在静默中迎来窗棂间透进的朦胧的晨光。
像是终于作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吴源忽然转过身抱住我的脸亲了一下,说:“玉,答应我,抓紧去做个妇科检查,好吗?”说着,便要起身下床。
“可你得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心里充满了疑惧,忍不住一把吊住他的脖子。
他只得重新坐下,迟疑了许久,才缓缓地掰开我的手,说,“玉,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这么样吧,你也别紧张。怎么说呢,你那儿可能是———封闭的。”
“封闭的?!”
我顿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血液也仿佛凝固了。
出了这样尴尬的事,他应该也是很灰头土脸的了。但他依然关爱着我,当晚就打电话来,说第二天要陪我去医院作检查,又劝我不必背太大的精神包袱,他相信这种病没什么了不起,应该还是可以做手术的……
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想不出一个好的理由来解释我为什么会突然了解到自己身体的真相,也担心姑姑会从蛛丝马迹中了解到我和吴源已经偷食禁果。她对婚姻抱一种十分严肃和古怪的态度,一直耳提面命我:交男朋友要“宁缺勿滥”,婚前决不能委身与人。虽然后来她对吴源颇有好感,依然常常提醒我:“盖掉郎家三条被,不知郎家心和意。”
所以,我暗自下定决心:在没有得到医生确切的诊断结果和处理意见前,我将不会和任何人———包括姑姑谈论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主动回避和吴源的一切联系和约见。
我要对自己的身体弄一个“水落石出”。
第一部分:封闭的下体黄鹤一去不复返
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我独自上了去南京的长途汽车。我决定到省城一家著名的军队医院做妇科检查。
在车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吴源总是影子一样跟随着我,我却无论如何看不见他。后来,我似乎来到一处山涧,正沿着涧边的石滩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身边是一片“哗哗”的流水声。忽然,山涧就走到了尽头,化作一潭碧绿的清水,水那边,突兀耸立起一座青山翠峰……我正自兀立间,身后陡起一阵嬉笑声。我听出是吴源,猛回过头去,但还未看清他的面目,他却早已凌空跃起,化作一道白练悄无声息地没入潭水中,再也没有露面。
“吴源……”我大声喊着,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再回过头,已不见来时的山涧和路,只感觉到扑面萧瑟的夜风。
我知道自己身处绝境,而那惟一伴我的人又“黄鹤一去不复返”,忍不住瘫坐在地,放声大哭起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哭了多久,只觉得嗓子已经哑了,眼睛似乎也快失明了。忽然就有一只大大的手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摩挲着。我以为是吴源,就一把抓住那手。然而,这却是一只枯柴般的只有骨节而没有肉感的手。我惊悸地扭过头,原来是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千秋老人,裹一身白绸站在我身后,又仿佛是漂浮在半空中。
“姑娘,不必伤心。我这里有张纸条,你仔细收着,自会找回心上人的。”
老人话音刚落,便兀自不见了,而那张狭长的白色纸条却早已攥在我的手中。我急急地展开来,上面竖写着八个墨迹未干的大字: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我不解其意,又抬眼望向半空中,却见那老人正从黑沉沉的夜幕后面探出头来,笑吟吟地向我挥挥手。我凝神看去,原来竟是父亲!
“爸爸!”我跃起身,失声叫道。
我的喊叫声没能留住父亲的身影,却陡然惊醒了我在车上的“黄粱一梦”。
我揉揉眼,直起腰,方发觉自己正成为一车人注意的中心。
但我依然神思恍惚,甚至感觉到父亲给我的纸条还紧紧地捏在手里。我于是疑疑惑惑地低下头,张开手———
那纸条忽然不翼而飞,但我在掌心似乎还能看到那八个醒目的颜体大楷: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113号,石玉!”我正这样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忽然就听到办公桌前的值班护士喊我的名字。
“有!”我慌忙应一声,站起身,紧走几步进得门去,在外间医生的办公桌前小心翼翼地坐下。
“你叫石玉,初诊,对不对?讲讲看,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问话的是一位约摸年过四十的女军医,剪着齐耳的短发,很精干、果断、利索的模样。她先稍稍翻了翻我的病历卡,然后才拿起笔,抬起头,很和气地望着我问。
“我想,”我说,犹豫了一下,才又道,“我下面———可能有问题。”
“白带过多是不是?”
“不。”我摇摇头。
“经血不正常?过多还是过少?”
“也不是。”我依旧摇摇头。
“经常性地提前或者推迟,对吗?这可是你们这个年纪的姑娘常有的事。”她胸有成竹地说,握着的笔已经戳到病历卡的纸上,似乎就要准备写下去了。
“不是。”我仍然明确地摇摇头。
她于是放下手中的笔,两手交叉搁在胸前的桌上,一脸困惑地望望我,然后道:“你总不会是说,你也染上性病了吧。”
“不,不是,这不可能。”我自觉到脸一红,忙加以否认,接着又小心翼翼,细声细气地道,“我是其它的问题,你看看就知道了。”
“好吧,那到里间去吧。”女军医于是站起身,手一指,引领我走到里面的小房间去。
“脱吧。”女军医“唰”地一声利索地拉上两床间的布帘,戴起医用手套,指示我躺到靠里墙的床铺上。
我低下头,剥笋一样一点点剥净下身,刚在床上仰面躺下,就感觉到医生的手———确切一点是塑胶手套———碰碰我的腿,用一种接近命令的口气道:“张开!”
我照做了。
“屈膝!”
我也立马服从了。
但也许张开得还不够,女军医又在我两腿的膝盖处压了压。
女军医开始在我的下面捏捏摸摸,动作算不上粗鲁,但也决不温柔……最后,她的手指终于搜索到了我小小的出口处,并在那儿停留住了,“石玉,你这出口处太小,我没办法用鸭嘴钳子撑开看看里面的情况。但我得用手指进去摸一摸,检查一下,这会有些痛,你得配合一下。”
“唔,好的。”我说,感觉到她的手指又滑移至我的敏感的部位,忙有些紧张地闭上眼。
折腾了大约五六分钟后,她才终于“抽剑还鞘”,“收枪入库”。
而我,则已是大汗淋漓,仿佛虚脱了一般。
第一部分:封闭的下体阴道横隔
强忍着下体的疼痛,我穿好衣服一拐一拐地走回外间,发觉女军医已经坐在桌前,正往我的病历卡上不住地记着什么。
“闭锁,阴道闭锁的一种。”她说,定睛望着我,又道,“如果再具体一点,则应该叫‘阴道横隔’。一般来说,‘横隔’大多位于阴道上端,中央或一侧有小孔,经血可由小孔排出。所以,如果不作妇科检查,人们通常并不觉察到,也不影响婚后的夫妻生活。但你的‘横隔’位置特别低,而且又很厚,几乎将整个‘门’都关死了。虽然这不影响你的经血流出,但要想过婚后的的夫妻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做手术呢?”我迟疑了一下,又忐忑不安地问。
“手术当然可以做。问题是效果很难说。主要是我们还搞不清你这种‘横隔’生成的具体原因。我手头几年前有一个和你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病例,手术过后半年多,很快又长合起来,再做还是这样。但大约因为一直有经血流淌的缘故,那儿也不至于全部封住,总还留有一个小小的出口。我们曾考虑过将口子开得更大一些,切除的部分更多一些,但这又有风险:因为只要这种赘肉的基础组织存在,你切得再多,开得再大,仍然还是会长合起来,只是时间会稍许长些罢了;可是,万一它被切除干净了,再不生长了,那儿又势必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空洞。空洞,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所以,姑娘,是不是要做手术,做什么样的手术,这关系到你的一生,必须慎重,要和你的家人仔细商量……”
我听得呆了,几乎忘却了下体隐隐的疼痛,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竟会走进这样一个进退失据的死胡同。
“这么说,我这是无药可救的了……”我喃喃自语,眼泪唰地漫涌而出。
女军医见状,忙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纸巾递给我,劝道:“姑娘,别难过,想开些。其实,不瞒你说,我姨侄女也有过和你类似的毛病,不过,性质不完全一样,她是先天的‘无阴道’,俗称‘石女’。大前年进大学前我给她做的手术,术后效果还不错,现在上海读书,已经有了一个日本男朋友。你要是决定了要做手术的话,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拿出一个最佳的手术方案的。顺便问一问,你现在是工作了还是在读书?”
“读书。”我说,擦净了泪,止住抽泣。
“哪里读书?”
“上海F大学。”
“是吗?我姨侄女也是F大学,今年大三,中文系。你呢?”
“也是大三,历史系。”我如实相告,忍不住也问一句:“她叫什么名字?”
“尹华。”
“这么说你是尹华的阿姨了?”我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巧的事。
“我是她小阿姨,她妈是我嫡亲的大姐。怎么,你们也认识?”尹华的小阿姨也很吃惊,眼神忽然亮亮的,说话的口气也变得分外地热情起来。
“不仅认识,还很熟呢。我们一起在学校体操队呆过,她是我们女生中年龄最小的。”
因为尹华的关系,我们聊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