һ���˵�ī��-��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ģ���������û�У��ȱ����ҧ��û�У���
������װ�������Աߴ�Ц��������˵��������˵��һ�����˶���һ�˴Ӷ�����ɽ��ɽ��ī�ѣ����˷ܣ���һ��Ҫ���ۿ�������һ��ʲô���ĺ��ˡ���Ȼ������һ�ۿ����ҵ�ʱ�����������������ںӱ�˯������Ҳ�֪���Ҹ�����������ʲô����ӡ����ֻ�о������ܸ��ˡ����˷ܣ����������ܶࡣ��
�������������һ�����Ļ��IJ���Ů��������ǰ����������ī��ʱ�����Ǵ������������Խ������ɽ����Խԭʼɭ�ֽ�ī�ѵġ���������ң�����������11�죬�����ͱ����������������߱߿ޣ���ȫû���뵽��ī�ѵĵ�·����˼��ѡ���ʱ��ֵ���£����Ƕ����ɭ�����������ܣ������������������¡��Խ�ī�Ѻ�����������û���߳�ī��һ������˵��ֻҪһ�������ī�ѵļ��գ��Ͳ��������ȥ��·����
������������˲���ѽ�����������������������ң����������;����������ô�죿����
�����������ţ�¶���˺����������ȣ��������ҧ�˵ļ�ʮ��Ѫ�ߴ��СС��������ز������ȣ������۲�λ��Ƥ�����Ϳ��¡���
������װ����˵������һ��ҩ�ƣ�Ϳ�ڽ��Ͽ������ס��������������Щ��ˮ������ϴ�ź�Ϳ��ҩ�ơ�����������������ͷ���������ң���ī�ѵ����ʱ������ȥ������Է�����Ϊ����Щ�óԵĶ�������װ����ȴ˵���Һ��������Ĵ����磬Ӧ��ȥ������Է�����������ÿ������������������һ��ԡ���
����һ�ᵽ�ԣ������ֹ������ҽ���������˵����������ľ��dz�һ�������档��װ������Ц����������æ����˵�а����ȸ�����һ�����������Ż����ӳ�ȹ�뿪�ˡ���
������װ���������ң������һλ����������ס��һ�𡣡�
������λ��ʮ����Ƥ����ڴֲڵ���װ������ȥ��һλ�߷����ˣ�80������ڸ�Ա��������ī�ѣ���������߾��سǴ�ɽԽ������ʮ���꣬ÿһ��ɽ����ÿ��ѩ����������ָ�ơ���˵������ī��������ô���꣬����δ��һ���˹�����Խī�ѡ������Ӵ����߽�ī�ѵ�������У�����Ωһһ����̽����Ӱ�ҵ����ݹ����߽�ī�ѵġ���
������װ������һ�����ˣ�Ҳ��Ωһһ����ī�����������ص���Ҫְ�ĺ��ˣ���ī���ػ�����س������س����칫�����ε�Ҫְ��Ա����ȫ���Ű����ˡ���
����ÿ��Ŀ�ɽ���ڣ���ī�ѵ������Ͽ�������ϵ��Ϊ���еļ��ڣ�����ȥȥ�ı�����������ڴ�Ͽ�ȵ��յ��ϣ�Ϊ�߷��ٱ�������Ʒȫ����װ���������š����䣬��װ������������æµ�жȹ�����
����������������Ŀ�ɽʱ�ڡ�˳���ı�����������ˣ����ͻ����ʯ������������������Ե�������˱������������Ͽ�ȵ��ˣ���װ�����ͻ�����ɽ��ˮ�������ֳ�������ī���ض������ƺ�������������ÿ��Ŀ�ɽʱ���������������Σ�յ���ʯ���У���ˣ���ɽʱ�ڵ���װ�����Ǽ�����æµ�ġ���
������������һֻ���룬��һ�����Ц�����ؽ����ˡ�һ�����������ڵĹ��������˱ǣ���������˼�����к�һ��������������������
����ī�ѵ���պ��ˣ�ľ������һ������������˶��ٵĵ���ݣ������˸����
��������װ��������ī����û�з����豸���������DZ߷������͵ģ�ÿ�����Сʱ���ڻ����˸�Ĺ����У���װ����������һֱ���쳣�˷ܵ�Ŀ�⿴���ҡ��Ҹ����ǽ�·;�ļ�࣬���ڰ����ԭ������ɽ���ʲ���ļ��š����Ž��ţ����ֻص�����;�ļ����У��˷�ʱ�������ڿ��в�ͣ�ػ��š���
���������δ���ҵĻ���һ������˵��������ˣ��������IJ����ˣ��ܳԿ��ͺ�����������ԭ�˵����ʡ���װ����Ц�Ǻǵ�˵����û��ȥ�������أ�Ҳ��֪���Ⱳ���ܲ���ȥһ�˰����
����ʱ����úܿ죬��װ�������������Ϣ������������ī�Ѻú�תת�������ؽӴ�һ��ī�ѡ���
������װ��������������ī�ѵĺڰ��У�ľ����һƬ��ڣ����ֲ�����ָ����
�����ҹغ���ľ�ţ���ͷ���������Ĵ����ϣ�ƽ�ľ�������������ܺ�ҹ�е�ī�Ѹ��Ҵ�������������ܰ��������
����3��һ���˵��ʾ֡�����
����ľ�����ľ���ϵ��ѵ������Ҿ��ѣ�����һ�����������ˡ���ƵĹ����Ӵ���������ڣ�ŨŨ���������Ų�ľ�ķ���Ʈ�˽������������������������緹������
����ϵ�Ż�Χȹ�Ĺ����ǽ����Ц�ų��ӱ���ȥ�������DZ��Ź�����ɽȥ�ˣ�ľ¥����һЩ����С���;���ľ���ڴ�Ͱ�ﵷ�ĻƾƵĸ�Ů�ǡ���������ң��Ű��帾Ů�����࣬����һ�㶼�����������ϵĺ��ӣ���Ҫ��ȫ�������¼��ո�ȡ����ף����˻ؼҺ�һ�㲻���¡�Ů������õ�ʱ����ǽ��ǰ�������ʱ�������õ�ʱ��ܶ��ݣ�һ���Ů����ʮ�߰���ͽ���ˡ���
�����߹�С�ž��������ס��ľ�ݣ�һλ����IJ�����̫̫���ڴ����Ͳ衣�������ҽ��ܵ�����λ�������˾��Ǻ���ס��һ����ϰ��裬��ר��Ϊ�ҵĵ��������Ͳ衣����˵���˴������ȵ����Ͳ裬��Ϊ�Ű�������Ҫ�Ǻ��������Ƶľơ���
�����ϰ���Ц�ų��ҵ��ͷ�����������������Ͳ裬һ���������ҵı������ϰ��������ı������Ұڶ�����
�����������Ư����ľ�ݣ���װ��������ͷ�����Ͳ裬���ҽ����������к������������ߣ��źõ�û�У����������Ҿ����Ÿ��������Ѿ������ˣ�Ҳ��ʹ�ˡ���
�������ղ����˵Ľ��ͷ�ʽ���Һ���װ�����������ȶ����ڵ�̺�ϣ����ϰ����������������Ͳ裬�õ��п���������������š���
������װ���������뵽����ȥ��������˵��ȥī�������֣����ҵı����ϸ�һ������ӡ�£���һ��ī�Ѳ����ף�Ҳ����һ������ôһ�Ρ�����˵��ī���ص��ʾ��Dz����ŵģ�ÿ�꿪ɽ�������ǾͿ��ϼ�������ڵı�ֽ����ī����صĺ�ͷ�ļ����������Ϲ��ںܳ�ʱ����ż���ī��������Щ��ֽ���ļ�һֱҪ�õ��ڶ��꿪ɽʱ�ڡ���װ��������˵����һЩפ����ī������ӡ�߾����±����������˼�ȥ�ź����յ�����ʱ���е��ѳ��˿츴Ա���ϱ�����Щ�ż���·;�о��������η�ɽʱ�ڡ������ī�ѵ�����ͨѶ����
����ī���س���һ��Сɽ�ϣ�ɽ�������ظ����ģ�ԶԶ��ȥ��ӭ��Ʈ������Ǻ��������Ŀ��˳����·�����ߣ���һ����ľ¥С�̵ꡣ��·�ľ�ͷ��һ������ƽ���Ŀ����أ�����ī�ѵ���ó�����á����Ρ��Ļ����ģ����ǰ������ƽ������ۡ��Ű����С���DZ���ʳƷ������Ʒ���������ó�ס�һƿ��ͨ�Ļƺ���ơ�ƣ���������ۼ۸ߴ�25Ԫ���������־��������ƽ�صĺ��档��
��������������һ�伫�����۵�ƽ���������ϰ��ʱ�䣬һ���Ű���С������������רע�ػ��ƻ�������װ�������ҽ��ܵ�������ī���������ֵľֳ���Ҳ�ǹ�����Ա����
������װ�������ҵ�������С����̸��һ�£�С����վ���������dz�������������֣��ò�̫�����ĺ�������˵���ԡ�������װ���������������ӡ���кܳ�ʱ��û���ˡ�������װ�������������ж����ˣ���װ���������ؿ����ң��������С���ظ����ң�������ֻ��С����һ���ˡ���
����С��������ľ���Ĵ���룬˫���ڳ����ڷ��ң��ó�һ�������ӣ����������ӷ�����öӡ��һһϸ�������ȡ��һö�����Ҹ���ʲô�ط�����æ�ͳ�һ����ɫ���±���������д��һ�λ�����˵������λ��ϡ���
�����ҰѱʼDZ��ݸ���װ����������װ����������������ֳ�����д�ڱʼDZ��ϵĻ�����һ�飬����˵�á���
��������������ֳ���ס����ī֭��ӡ�£����ظ�����д���ּ��ıʼDZ��ϡ��Ҽ����ý�����ס�����֣�С����һ������˵�����һ��ǵ�һ��Ϊ����̽����Ӱ���˸��¡���������
����4�����������������ͼ��������
�����ҿ�������߳��յ�����ľ¥��������Ҫ�����߽��Ű����˵ļ�����Զɽ�����ϡ�ɱ�������������ľ¥����Щ���ϵ�ľ¥���Զ��ī�������ĵĻ����ϡ��Ҿ���ȥ���������
���������������¼ŵĻ��£��Ҿ���ط��֣�����ľ¥����������֦Χ֯��һ����Ȧ��Ȧ�ڵĺ���������������Լʮ���صĴ�ϡ���Щ�в������ĺ�Ƥ���ϣ����������������������ʵĺ����ϣ�������������ij�ԡ����
����ľ¥�ڲ�֪ɶʱ���߳���һ��Լʮ����к���ͷ����б�ش���һ����ñ������һ˫�dz������Ŀ�⿴���ҡ��ҳ������ͷ���ֳ��������֡��к�ת��Ѹ���ܽ�ľ¥���ҽ���������ľ����ȥ��ľ¥�����ܳ�������Ŵ��ۡ��米�������к����ҳ����������֣�����˵�����Ǻá���
����ľ���ڵĵذ��Ϸ���һ���п��ĺ�Ƥ��ϡ�������ָ���п��Ĺϣ���ָָ�ҵ��졣һ��С�к��������ó�һ�ѷ�����ذ�ף�����һ��ϸ��ҡ��Ұ��ǿ�Ϸ��ڱ�ǰ�����ţ�һ�ɵ��������㣬��ҧ��һ��ڣ�������ɬ����
������ʱ��һ��һŮ�������Ŵ����Ű����˳�ľ¥������������װ���˻Ƴγε����װ��ӡ���һ��һŮ���Ӻ�С�����ڱ��ϵı���ȴ�ܴ����������ر��Ŵ�����ľ¥������
��������������ľ¥�����ˣ�æ�ó�һ�������������Ŵ��ߵ�ľ¥��ͷ����б�����ӣ��������ؽ����װ����㵹�ڵذ��ϡ������˳���������һ�ڴ�������������㶡�Ů���˹���ľ���ϣ������װ���̯��������к��ܹ�ȥ�������װ��Ӷ��ϣ������ذ�������������
�������ݵ������������㲣��������磬����Լ��ʮ�ꣻС����Ů����Լ��ʮ�߰��ꡣ�������Ͽ������˵��������ܴ�
����һ���������������Ĩȥ������ͷ���Ⱥ������Ƶ����Ҵ���������ʲôʱ����ī�ѵģ����˳Ծ����ǣ���λ�����˲�����˵�������˵���DZ��Ĵ�������
�����Ҹ������������Ĵ���˵�ú��������һ��ǵ�һ�����Ű�����˵�Ĵ���˵����ô�á���ȴ����ľ������Щ��������ӳ�ý�����������װ��ӣ���˵����ī������ط��ֵúܣ����װ���������գ�ÿ�궼�кܶ��������ڵ������
�����������ջ���ô��������ô�ԣ���˵������ƺȡ���
����������������˵�������Ĵ�����������ѯ���˺ܶ����������飬������������ҽ��ܡ������ᵽ��Ƥ��ʱ������������Щ��Ƥ��Ͼ��Ǻ���˵�Ļƹϡ����治�����ţ���Щ��Բ��˶�Ĵ�Ͼ��ǻƹϡ���
����̸���䣬Ů�����ֱ���һ�����װ�����ɽ·�����������������������С������Ů����Լʮһ���꣬���ǹ��Ž�Ѿ������ͷ��һ��һ���س�ľ¥��������
��������ʱ�֣������˽��������ҳ��緹����˵��������Ϊ����һ����ƹϡ��ҳ������̻ҵĺ��ݿ������������ʯ������������ԣ�һ�������������ݽ��䣬ľ���������˵ļҲ�����һ�����ࡣ����ߣ�����һ����С��ľ�ţ�������һ�����֣�δ�����ĵ����Ѷ����֡���
�������������ˣ��������ý�������������˵�Ѿ�������һЩ�����繻���ˡ���ָ������������������Ů��˵���������������¡�������ת����Ů���˺���������Ů��˵��ʲô��Ů���˺�����Ů���Ǿ�æµ��������
������ȥ��Ƥ�Ļƹϰ������ģ����ϵĻ�����������ҵ�����ʯ���ס��ܿ�أ�ľ���������˹�������㡣��
�������극��ͬ���е��Ű�����һ�������������һ��Ȼƾơ�Ů���˺���������Ů����������ɹ̫�����Ҷ������˺ܸ���Ȥ����Ȼ�����������ݣ����������ҽ�̸ʱ˼·�dz�����������һ���������Ĵ������ҷѽ⡣��
����ͻȻ�����Ժ��г���һ�������ǰ��λ���������˲��DZ����ˣ�����һ���صص������Ĵ��ˣ�����һ�����Ǵ�Զ����������������ˣ���
�������ҵ�һ��ѯ���£����������ڵ�����ʵ�顣��
�����������ճ£���ʵ�����36�꣬�����Ű����ˣ�����һ���������Ĵ��ˣ��ϼ����Ĵ���������
����1985��ij��ī���ؿ���ӡ�ȱ߾��ı߷�վ��Ա��һ���ϱ���������Ա���ϱ��Դ��Ͼ�װվ�ڱ߷������ĸ�λ�ϵ����¾�װ��Ա�뿪��λ��������û��ȥ��ī���ء��ڹ�;�У���Ҷ���ȥī���سǿ�������λ�������紧���Լ��ĵ���������һ���߽������滷ɽ��ī���سǡ���
����ī�����س���λ�صص������Ű����ˣ����ò�̫��������ͨ������ȫ�������л�ӵܱ�Ϊī���صķ�չ������Ŭ������˵�س������Ա���������ǿ����ī���سǵ�δ����չԶ���������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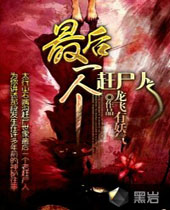
![[�촩]����һ���Ƿ���](http://www.nstxt.com/cover/0/7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