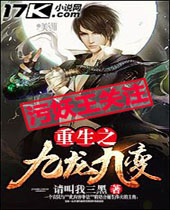地狱变-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孤独地游荡在黑暗里,触摸虚无的空气——实际是日渐稀薄的氧气,越来越多来自地底的腐尸之气。我睁大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仿佛绝望的瞎子……忽然,眼前闪过亮光,如同一万个太阳般明亮,那是世间最美最奇幻的景象,转眼让亘古寂静的盐化荒漠,变成月球般的彻底荒凉。我躲在观察掩体深处,举着沉重的军用望远镜,观察数十公里外的核试验。当周围所有人欢呼成功时,我看到父亲的眼里含着泪水。很多年后,我一直试图搞清楚当时父亲的泪水究竟是因为喜悦还是悲哀,如果属于后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妈妈,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我不是身处一百余米深的地底吗?不是在世界末日人类最后的幸存者之中吗?可是,无论我怎样揉眼睛,始终看到这幅将近四十年前的景象,被大脑掩埋如此之久的记忆——那是柴达木盆地最荒凉的中心地带,地球上真正的不毛之地。
父亲,我依然那么爱你!即便我年近半百。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没有在世界末日中死去,你仍然好好地窝在躺椅里,头脑清晰地回忆着四十年前,那个美好寂静的夜晚,在清澈得几乎透明的荒野星空中,为我指出哪一颗是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哪一片又是遥远依稀的猎户座星云。
我的儿时记忆中很少有父亲,他总是躲藏在某个邮政信箱背后——没有地址也没有单位,只有一个特别的号码,如果给他写一封信,要两个月后才能收到,在几千公里外的新疆或青海。当时没有电话,连发电报也不可能。有一回,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上面明显有被人涂改的痕迹,显然担心他泄露国家机密。
其实,父亲这封信只是告诉我,我家祖先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的子孙默默无闻,直至乾隆年间有人进士及第才飞黄腾达。道光时我家先人做到翰林编修,四兄弟皆以诗词闻名。我的祖父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经商致富。父亲抗战后赴美攻读理论物理学,是爱因斯坦的得意门生。五十年代,父亲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位,追随钱学森先生归国,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自从我出生以后,他一直隐藏在沙漠中心,记录与研究每一次核爆炸的数据。至今,两弹一星元勋功臣名单里,还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那一年,我的母亲自杀了。
我的外公是著名历史学家,我的母亲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上古文明起源。母亲的研究与众不同,她关注国外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时中国学术界认为,北京猿人、蓝田人、元谋人是现代中国人直系祖先,我们单独在中国本土进化为人类。但母亲大胆地提出新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与其他种族一样,无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来自十几万年前的非洲。而北京猿人早已如尼安德特人般灭绝,与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亲缘关系。她的观点震惊了学术界,被定性为洋奴哲学、中国文明外来说翻版。她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北大学生告发她是苏修特务或美帝间谍,是帝国主义及社会帝国主义消灭中华民族的急先锋。母亲在被自己的学生殴打几小时后,爬到寒冬腊月的未名湖上,破冰溺水身亡——我亲眼看到妈妈的尸体从冰冷的湖水中捞出来,像永不醒来的睡美人。
那一年,我十岁。
我独自离开了北京,偷偷爬上一列运货的火车,饿了三天三夜,撑到了西宁。几个月前,数千公里外的父亲,突然被调离了氢弹项目,奉最高统帅的指示,深入柴达木盆地的荒漠,参与名为“101工程”的神秘项目——这是父亲邮政信箱的编号。
在寒冷的高山与草原间,我沿路乞讨求生,几次饿得昏过去。一户蒙古族牧民救了我,他们不知道什么“101工程”,只知道在荒野彼端,常有解放牌卡车出入。我跟随着他们,沿着卡车深深的辙印,穿越只有藏羚羊的无人区,来到一片真正的不毛之地,传说中的永久性地堡。荷枪实弹的士兵将我抓到地下指挥部审问,这才见到了父亲。
他没认出我来,我却认出了他。当我说出他和妈妈的名字,他惊讶地把我抱在怀中——他不知道妈妈已经自杀了。
父亲温热的泪水打在我脸上,从此我就住在“101工程”基地。
这里距离核爆试验场最近,有一个警卫连,父亲是唯一的研究人员。荒漠里有大把空闲时间,父亲不像其他人那样热衷于猎杀藏羚羊,他成为了我的老师,除了最擅长的数理化,还教授我语文、历史、地理。我在十二岁时,几乎已达到了物理学研究生的水平。父亲从不说他的研究内容,每到天黑就强迫我睡觉,而他钻进可以防御核辐射的实验室,一熬就是整个通宵。
有一次,父亲破例允许我参与观察一次核试验,他给我穿上全套防护服,戴上厚厚的眼镜,藏在坚固的掩体里,通过一个狭窄的口子,用高倍望远镜近距离观测核爆。核试验相当成功,第二天震惊全球,据说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目瞪口呆,撤销了本已拟定好的毁灭中国的计划。永远不会忘记那巨大的光芒与火焰,似乎只要再等几秒钟,就可席卷到我脸上,进而摧毁整个世界。当我擦着父亲脸颊上的泪水,回想刚才那道光芒——就像新年焰火般绚烂夺目,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只有等到那一天,才是地球最盛大的节日。
那天以后,父亲开始向我开放他的研究成果,包括最新的地球物理勘探数据。怪不得每隔几天,荒野上就会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并感觉脚底剧烈震动。核爆不可能如此频繁,肯定有其他原因——他们在用炸药引发人工地震,通过地震波向下传播,勘探地球深处的秘密。许多矿产资源就是用这种方法找到的,但他们并不找矿,而有更重要的目标。父亲制造的人工地震威力强大,可以达到自然地震的烈度。幸好方圆数百公里内渺无人烟,否则再坚固的建筑都会倒塌,而我们也只能住在地堡里。
有一夜,核辐射没有超标,父亲不穿任何防护装备,独自带我走出地堡。我们躺在一块高丘上,仰天看着清澈的星空,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亘古荒无人烟之地,所有星辰都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爸爸,这些星星将永远存在下去吗?”虽然身下是坚硬的岩石,气温冷得让人直流鼻涕,但我依然十分享受。我想,那是我人生中唯一感到幸福的时刻。
“不,虽然叫恒星,但也不是永恒的,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出生也有死亡。”
“星星会死吗?”不知为何,我的脑中浮现起了妈妈的尸体,从结满冰块的未名湖里捞起的妈妈。
“是的,偶尔运气好的话,这里还可以用肉眼看到超新星的爆炸——恒星死亡过程中的爆发。”
“我怎么看不到?”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的。”父亲微笑着摸摸我的头。
他的手好大好暖和,暖到了我的心窝里。可是,我悲伤地问道:“如果,连恒星都会死亡,那么地球也会死亡吗?”
突然,一串流星划破夜空。
父亲异常严肃地回答:“是,太阳必将死亡,地球也必将死亡,人类也是如此。”
“爸爸,我害怕。”
十二岁的我真怕了,比亲眼看到妈妈的尸体还要害怕,比流浪在饿狼出没的荒野还要害怕,我是害怕到了所有人都将死去的那一天,那些害死我妈妈的坏人,和所有的好人同样死去,死得没有任何差别!
父亲把我抱入怀中,口中呵出大片热气,自言自语道:“人生是什么?我们生下来,然后又死掉。”
不久,我从父亲口中知道了他的秘密——所谓“101工程”的研究对象,并非核武器或洲际导弹,而是地球将于何时毁灭。不是毁灭于美苏核战争,就是毁灭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或是毁灭于自然灾难本身。只不过,到时候不分什么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分什么一小撮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或是世界上四分之三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反正是一起灰飞烟灭。
父亲在观测核爆数据的同时,也发现最近十几年来,地壳活动越来越反常,各种灾变也因此不断,甚至预言到了几年后的唐山大地震。虽然,“101工程”只是最高统帅不经意间的一个指示,父亲却彻底迷恋上了这项工程,以至于数年间再没离开过柴达木盆地,日夜与人工地震和密密麻麻的数据,以及让人孤独到绝望的星空为伴——要不是有我陪伴,他早就走火入魔了。
父亲的研究不但深入地底,还指向了天空——上头给他配备了最先进的无线电设备,可以直接将信号发射到太阳系以外。他坚信自己接收到过神秘的电磁信号,只是限于技术障碍无法破译——简而言之就是外星人的信息。
那年,我十三岁。
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入巨大的“101工程”,以及父亲的世界末日研究,都被当作荒诞不经的胡闹而被撤销。父亲不愿离开地下研究所,在所有人员都撤离以后,我们父子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还想继续整理那些令人震惊的数据,直到消耗完所有补给,在大雪中等待死亡降临,才有一队军人把我们救了出来。父亲被强制送回北京,继续从事核武器研究,而他数年来艰苦采集来的数据,却被轻而易举地销毁了。
他疯了。
我本以为父亲活不了几年,没想到他在精神病院里活了三十多年,至今依然坐在躺椅里,从早到晚为病友们描述核爆炸的情景。半个月前,我专程去看过父亲一次,他差不多已认不出我了。我紧紧抓着他的手,看着他混浊的双眼,仿佛回到柴达木盆地的荒野,看着他遥望星空的目光——很遗憾我无法抱着老父的骨灰去墓地,因为他必将活得比我长久。
我的时光已所剩无多。
今年一月,我在美国参加世界末日学术研讨会时,晕倒在万人瞩目的讲坛上。美国最好的医生为我作了诊断,确认我的脑中有一个恶性肿瘤——运气好还能活半年左右。
最初的愕然过后,我从容接受了这个结果,嘱咐医生将病情绝对保密。我放弃了治疗,只是随身携带一些止疼药片。医生无法判断我得病的原因,而我自然想到了那片骇人夺目的光芒——是我十二岁那年,近距离观测核试验的结果?因为遭到核辐射而突患脑癌的病例很多,比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救援人员,有人在几十年以后突然发作,但也不排除一辈子都安然无恙——比如观测过多次核爆,却健康活到八十岁的老父。
我并不遗憾生命如此短暂,也不遗憾没有家庭与孩子,甚至连真正爱过的异性也没有。令我自豪的是,从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能像我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我本就不在乎。我可以掀起一场影响数亿人精神深处的运动,各种肤色各种国籍各种阶层的人们,都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尽力安排好自己身后之事,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弘扬人类大同,这何尝不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我,便是他们的神。
我唯独有两个遗憾,一是无法为父亲送葬,二是不知能否看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就像我等了一辈子,都没有凭肉眼看到过超新星的爆发。
对不起,相信我并崇拜我的读者们,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等待这一天,无比强烈地期盼世界末日到来——自从母亲的尸体从未名湖中被捞起来的那个雪天以后,自从亲眼目睹核爆的一万个太阳的光芒以后,自从与父亲躺在黑夜的荒野里讨论恒星的死亡以后……在真正的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我想选择一个最具有潜质的地方。我不想选择地震高发区、活火山口附近、地质灾难易发地……他们会说我是故意挑的,我想找到一个熙熙攘攘的闹市,一个最不可能发生灾难的地方。
未来梦大厦。
我调查了中国东部沿海所有城市的地质结构,发现本市最近数十年来地面沉降严重,尤其是这座大厦附近的区域。我私下里作了监测,确认这座大楼正在严重下沉,再加上市郊的化工厂近年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市区地底出现了一个巨大空洞。如果有一些外部条件,就会发生严重的地质灾害。于是,我选择了这一天,愚人节,大雨之夜,独自来到未来梦大厦,进入卡尔福超市地下二层——这样就有了回到地下避难所的感觉,站在摆满我的作品的书架前,祈祷灾难发生……是我感动了上帝吗?如果,你存在的话。
4月1日。星期日。夜,22点19分以后,我相信了。
我还让地下所有的幸存者都相信了世界末日的到来。那些人都深信不疑,并把我视为最后的救星。
这是命运给我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