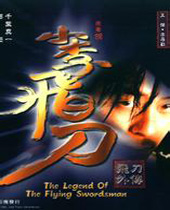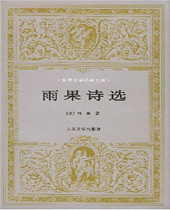吾师余秋雨-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么一个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最早高声地要他坦白交代的年轻造反派,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静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我一见这个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但却想以此向眼前这位亲手送走九个儿女的真正强硬的女性,作一种保证。我估计此刻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生了病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祖母和叔叔的骨灰早已移回故乡,与爷爷和其他亲人葬在一起。去年春天,我又把他们的坟墓重新修了一次。
站在故乡的青山间我想,直到现在才知道,长辈的亡故不仅仅使我们一次次伤心,而且还会使我们的一段段生命归于混沌。没有问明白的秘密再也问不到了,连自己的各种行为因果,也失去了参证。原以为周围拥挤过无数双可以参证的眼睛,到后来才知道,最后一双往往只属于某个长辈,而且已经闭上。
其实又岂止是参证,长辈的眼睛也是我们人生险径上的最后可以依赖的灯。没有这些灯,当初的路就很难走下去:现在熄灭了,连当初的路和当初的我们,全都沉入黑暗,成了疑问。因此,长辈的亡故,是我们生命的局部沉沦。
我祖母和叔叔的坟墓是余家最近一次大劫难的见证,祖母因长寿,还成了历史转折的苍老刻纹。由此联想到,那个惊心动魄、血泪纵横的历史阶段,大多已化作青山间的万千土堆,不再作声。世间文字,究竟是记录了还是掩盖了那种曾经刻骨铭心,现在却已远去的声音?
说到那场劫难,那么,我所说的长辈,已远不止是亲人。无论在劫难中还是在转折中,我们都曾遇到过一些非亲非故的长者的目光,温暖、慈爱、公正,有时也许受人挑唆,怒目失当,但一旦细睹,却会顷刻柔软,回归人性。正是这种长者的目光,在劫难中留存了依稀的公正,在劫难后分辨着混杂的是非,使时时可能失序的一切变得有序,使处处可能张扬的邪恶受到节制。
这样的目光自然也会让人有些害怕,使他们难于长时间地胡乱整人。因此这些人只能耐心等待,一等几十年,等到所有公正的历史见证人逐一亡故,然后,在失去见证人的天地间递补为“见证人”。摆脱了多年来别人的警惕逼视,他们深感痛快,重新开始点燃早已熄灭的老火。我曾看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先在报刊上诬陷我,然后又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要说明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连历史也要听命于他们的狞笑。
旅行,家人,亲情(5)
逝去的老人确实已经不能为历史作证了,但也绝不会为这些人作证。我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灵性,真言谎话各有报应。我相信九天之上会有很多长辈的眼睛,大地之间也有很多能够用最朴实的直觉分辨真伪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的祖母,不留名又不识字的祖母,会不会在冥冥中遇到一再称赞过她把我的名字取得很有诗意的车部长和冯岗先生?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刚烈的余志士先生,会不会
在青山间与当年的打手们狭路相逢?也许,正是当初强迫叔叔“忏悔”而逼他自杀的打手们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相反的把柄,会诱骗一二个无知的小喽罗出来喝令叔叔“忏悔”?叔叔当然不去理会,却会忧郁地转过身来,看看尘世间是不是也有这种跨代的孽债。
我仿佛接收到了叔叔的目光,于是告诉他:“安息吧,叔叔,这尘世间真是好多了,你看他们老老少少折腾了我这么久,我还能悠然走笔、信步天涯。”
祖母一定又会称赞我的强硬,这次我可要谦虚了,说:真正该称赞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1)
他总是不放弃他的使命感、责任感。走得再远,看得再多,他的定位没有变,他要把中华文明作为自己思考与研究的依附点的信念没有变。他似乎对这样一段文明的延脉、这样一个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了肯定和希望。
“千禧之旅”归来他说:“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一直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
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欧洲之行归来,他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它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这样的话语,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几大文明进行实际的考察与比较、还没有发言权的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坚决和勇敢的事情。
这是他的世界观使然吧。总是这样,勇敢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从不轻言放弃与绝望。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选择那条积极的路线。就像他看待爱情一样。
曾经有一次,一个很常见的中国现实话题的议论,让我忽生愤懑与决绝,我甚至认为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状,只有依靠外力。当然国家主权不能丢,但管理层要全部由有过来经验的外方控制,所有规范、准则要对中国人强制执行,要从零开始,强制大家改变骨子里的劣根性。否则要靠“自我改造”,不知又有多少好时光被荒废掉了。现在总说要“接轨”,哪那么容易就接上了。
他笑我,摇头说不对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殖民地”的结局就是什么也不是。你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我绝望地说,我不是光指责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就像我走在澳门、香港的街上,老忘了身处何方,哇啦啦一嘴说不完的话,看见马路上没车就想要过去,倒是周围本地人的安静、乖乖立在红灯下等待的样子,突然就提醒我,我有多么的丑陋,那个时候也一下就把我和当地人划分了开来。
他越发地好笑,说这说明你还算是有点慧根的。
我又开始攻击街上的建筑、城市规划,连带每年一次的春节晚会,绝望得不得了,主要是觉得浪费那么些钱,做点什么不好。好像常去国外考察的倒成了我了。
他有时也会很同意我,但没我这么偏激,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听上去比相对年轻些的我更有感情。比如春节晚会,我一听说有人想请他做顾问,就要他把所有那些土人全部赶走,找一些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一些有现代意识的实力派,从灯光、造型、服装,到演出内容、形式全部翻新,要真正能体能现在中国人的艺术水准的。他听得更好笑,说你对晚会的期望值太高了,它只能是一台通俗的普通老百姓要看的晚会,办了十几年,它已经是一个传统,一样习俗了,你不能要求把传统和习俗都彻底推翻。它现在就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必上的菜,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但一定要摆在那里,图个热闹。
可是有多少人投入其中,要花多少钱啊。我说。
我们谈到现在的白领,他对他们倒是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在日常中领略最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触到最现代的领域与人才,将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行为、风尚。
我却依然悲观,一是他们人数太少,二是我担心他们一走出写字楼汇入大街上的人流,原先的许多本性就会被迫呈现。像我这样一个自以为蛮有点自律意识、经常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还时不时地会没于大环境中浑然不觉,更何况那些必须要在现实中求生存并养活一家老小的人。
他跟我说到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人,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舒适和舒心。脱离了一个文化的母体,人如浮萍,即使是拿到一个国际大奖,也无法彻底改变生活的境遇和精神的境遇。他说他在境外遇见一位作家,大家都以为他该春风得意忘乎所以,但他不完全开心,一提起祖国大陆眼睛就要红,就想要哭。更有一些完全不愿意了解一下中国国内现状的人,对现在国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里的变化完全不清楚,人已经很老了,还生活在自己臆造出来的假相里,是很悲哀的。
我说这些事我也听到过一些,我很替他们伤感的。我的一位女友是出版社编辑,手里有一部某著名作家前妻的小说稿,就是写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境况,其中也写到他们婚姻的失败,写到那位作家与别人国家的主流社会完全不相融的事实,还有他们的孩子在西方社会里的迷失。她讲给我听,我听得都有些难过,老么喀嚓眼的,还要搞那样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折磨,真正是一团糟啊。我曾鼓动女友干脆把书做成纪实性的,再打上那位作家曾经创作过的几部小说名,做成中国流落海外的文人心态史、精神游历什么的,保管畅销。但是我的女友很有职业操守,作家和作家的前妻都是她的朋友,她不能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还愿意把书做成一般的小说,情愿它淹没在嘈杂的书市里无人问津。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我说我只是可惜了那小说后面的文化背景。
不过我一狠心又会想,一些人留在这里,到头也可能就堕落成无所事事靠国家养着的无聊文人,装模做样的,还动辄内耗生事,还不如把他扔到国外去自食其力,好歹也算是有事可做。
在余秋雨还在走着“千禧之旅”时,本土突然刮起一股“倒余”风,当时我和“博物馆”剧组的人甚至想要往南亚那边打电话,表示我们的声援,只是无法联络他才作罢。那时也不知马兰电话,后来从《千年一叹》里看到,凤凰台安排马兰中途前往南亚与余老师相聚,分手时马兰哭得很厉害,我想她的眼泪里肯定有独守在国内目睹丈夫被流言飞语围攻的委屈和疼心。
几个月后余秋雨随车队刚进入国内,马上有记者各种各样的追问包围住他。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他说。
多么难过和失望的感觉。
但他还不轻言对整体的绝望,依然兴致勃勃地念叨:“它们的出现不